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是我们投产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。一天下午,质检组的老王,一个平时话不多的老师傅,皱着眉头抱着一小箱零件来到我办公室。他把箱子往我桌上一放,哐当一声,没说话,就那么看着我。我拿起几个零件仔细看,有的是边角有毛刺,手感糙得很;有的是尺寸稍微有那么一丝丝的偏差,不仔细量根本看不出来,但装到整机上就是会有点别扭。
“王师傅,这一批……多少?”我问他。
“抽检了三百个,不合格的,差不多这个数。”他伸出巴掌,翻了一下。
十个点。我的心当时就沉了一下。百分之十的不合格率,意味着每一百个产品里,就有十个是残次品。它们要么需要返工,耗费额外的人工和时间,要么就直接报废,变成一堆废铁。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,更像一记耳光,打在我那个“做好产品”的梦想上。那天晚上,我看着车间里那些默默运转的机器,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机器是好的,工人兄弟们也都在认真干活,可为什么出来的东西,就是达不到我心里那个标准呢?
光着急没用,得找出路。我和几个骨干,那段时间几乎长在了车间里。我们围着生产线,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看,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摸。问题一点点浮出水面:老张那边,进料检验就靠一双眼睛看,标准全凭经验,忙起来难免有疏忽;李姐的冲压机,用了有些年头了,参数有点飘,稳定性不够;组装线上的小年轻们,手法快是快,但有些细节处理,比如螺丝拧的力度,全凭手感,劲儿大了小了都没准头。
说白了,我们的生产,太依赖“人”了。人的经验是宝,但人的状态会有起伏,会疲劳,会出错。这么干下去,质量永远像坐过山车,时好时坏,根本谈不上稳定。
改变,是从最笨的地方开始的。 我们决定,先从“规矩”立起。
第一板斧,砍向了原材料。我们搞了一套详细的进料检验标准,不再是“看着没问题”,而是白纸黑字,尺寸、材质、表面光洁度,达不到标准,谁说情也不行,一律退回。为此还得罪了个老供应商,但没办法,源头的水不清,后面流的只能是浑水。
第二板斧,是对着设备去的。那台老冲压机,我们下了血本,给它加装了一套高精度的数控系统。调试那天,老师傅围着它转了半天,嘴里嘟囔着:“这玩意儿,比我还准呐!”虽然花了钱,心疼,但看到它压出来的每一个零件都像复制粘贴一样标准,我觉得这钱花得值。我们还给几台关键设备制定了严格的保养计划,就像人要做体检一样,定期检查、上油、更换易损件,防患于未然。
最难的,是第三板斧:改掉人的老习惯。我们在每条产线的关键工位,都挂了醒目的作业指导书,不再是以前那种笼统的文字,而是配上图片,甚至拍了短视频,每一步怎么做,做到什么程度,一目了然。我们还弄了个“质量曝光台”,不是要罚谁,就是把每天发现的不合格品摆上去,让大家自己看,一起分析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。一开始大家还有点抵触,觉得不自在。但慢慢地,氛围变了。工人们开始互相较劲,比谁出的活儿更漂亮。组装线上的小王,自己琢磨出一个小工具,能让螺丝拧的力度刚刚好,我们马上就在全车间推广了,还给了他一笔小小的奖励。那一刻我明白,当大家真正把质量当成自己的事,劲儿就往一处使了。
这个过程,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有工人觉得新规矩太麻烦,效率慢了,私下里有怨言;有新设备水土不服,调试了好几次才稳定;为了达到那个99%的目标,我们不知道熬了多少夜,开了多少会,反复测试、调整、优化。有时候看着仓库里那些因为标准提高而被判为不合格的旧库存,心里也挣扎过。但每当我想起老王放在我桌上那箱零件,想起用户可能因为那一点点瑕疵而产生的糟糕体验,我就知道,这条路必须走下去。
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,我们又做了一次全面的质量统计。当报表打出来,我看到那个数字——产品合格率99.2%——的时候,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车间主任笑着递给我一个刚下线的产品,我拿在手里,反复地看,边角光滑,严丝合缝,透着一种工艺的美感。
那一刻,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,听起来都格外悦耳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,用将近四百个日夜的坚持和汗水,换来的底气。现在,我们的产品出厂,我心里是踏实的。我敢对任何一个客户说,这东西,靠谱。
这条路,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。99%不是终点,只是一个新的起点。但我永远会记得,我们是如何从那个百分之九十的泥潭里,一步一步,笨拙却又坚定地,走到了今天。做好一件东西,没那么复杂,无非就是敬畏手艺,死磕细节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也对得起别人的信任。这,大概就是我这个笨人,能想到最聪明的办法了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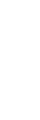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