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了。整整三年,每到这个季节,我都怕从这棵树下走过。
这棵桃树,是奶奶亲手种下的。那会儿我还在上小学,个子还没锄头高。奶奶握着我的小手,一起把树苗埋进土里。“囡囡呀,”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,带着泥土一样的温和,“等这树开了花,结了果,你就能吃上甜甜的桃子了。”她的手粗糙得很,满是老茧,硌得我小手痒痒的,可那份温暖,却一直透到我心里去。
奶奶没读过什么书,一辈子都住在这个小村子里。但她认得桃花,会念好些关于桃花的童谣。春天的时候,她喜欢搬个小马扎,坐在树下做针线活。我呢,就趴在她膝头,听她哼那些调子。阳光透过花枝的缝隙,在她花白的头发上、满是皱纹的脸上,洒下细碎的光斑。那时我觉得,奶奶会和这桃树一样,一直一直陪着我。
桃花一年一年地开,我一年一年地长高。后来我去县城读中学,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每次回来,奶奶都会站在桃树下等我,手里要么揣着几个刚煮的鸡蛋,要么是几块她舍不得吃的点心。桃花开的时候,她会小心地捡起最完整的花瓣,夹在信纸里,托人带给我。信上总是那几句:“囡囡,好好吃饭,奶奶想你。”那花瓣压在书里,时间久了,会变成半透明的,薄得像蝉翼,却还留着一点点若有若无的香。
我考上大学那年的春天,桃花开得特别盛,密密匝匝的,几乎看不见叶子。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,在树下站了很久。她摸着粗糙的树干,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对我说:“咱们家的囡囡,比这花儿还有出息哩。”那时我只顾着兴奋,要去更远的地方,看更大的世界,完全没有留意到她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落寞,和她越发佝偻的背影。
就在那年秋末,奶奶病倒了。我赶回家时,她已经说不太出话了。她静静躺在床上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窗外,桃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,光秃秃的枝桠在冷风里摇晃。她紧紧攥着我的手,嘴唇动了动,我俯下身去听,只听到极轻的几个字:“桃花……好看……”
她到底没能等到下一个春天。
奶奶走后的第一个春天,我回了家。推开院门的一瞬间,我愣住了。满树的桃花,就那么毫无预兆地、泼辣地盛开着,粉红一片,灼灼其华。它们开得那么热烈,那么不管不顾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邻居都说,今年的花开得比往年都好。
可我的心,却像猛地被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我一步一步挪到树下,抬起头。阳光还是那样好,花瓣还是那样轻盈地飘落。可树下,再也没有那个等我的人了。再也没有人会小心翼翼地把花瓣夹进信纸,再也没有人用那双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发,再也没有人慢悠悠地喊我“囡囡”了。
我扶着粗糙的树干,终于忍不住,放声大哭起来。泪水模糊了眼前这片绚烂的粉红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,什么叫“物是人非”。这世间最残忍的,不是失去,而是曾经承载着所有美好记忆的景物依旧,那个与你共同创造记忆的人,却永远不在了。桃花不懂人的悲伤,它只管自顾自地年年绚烂。而我的心,就像那落了一地的花瓣,看着还是完整的形状,轻轻一碰,就碎成了粉末,再也拼不回去了。
后来,我读到了那句诗: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短短十四个字,像一根细针,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痛的地方。古人早就把这种滋味写尽了。
如今,我又站在这里。风大了些,花瓣落得更急了,真像下了一场粉红色的雨。我蹲下身,从泥土上捧起一些花瓣。它们柔软、冰凉,带着一种凄然的美。我没有把它们扫掉,就让它这样落着吧。奶奶是属于这片土地的,这些花瓣,就当作是它们替奶奶,静静地陪着我。
桃花落了,明年还会再开。可我心里有个地方,永远地缺了一块。那块空缺,是关于奶奶的所有记忆——她的温度,她的童谣,她看着桃花时温柔的眼神。它们没有消失,只是化作了另一种存在,像这些融入泥土的花瓣,成了我生命的养分。
我站起身,最后看了一眼这棵桃树,转身离开。花瓣还在身后无声地飘落。我知道,往后的每一个春天,我大概都还是会疼。但这种疼里面,开始有了一点别的东西。它让我更真切地记住,曾经有人那样深地爱过我,那份爱,就像桃花曾经绚烂地开过,它真实地存在过,这就够了。
心碎了,就碎了吧。带着这破碎的心,也一样可以走下去。就像这树,年复一年,既承受着最绚烂的花开,也默然接纳着最彻底的花落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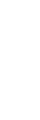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