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它了。我对自己说。
我的第一个“世界”,简陋得现在想起来都想笑。工具?没有。就是一个吃完了的黄桃罐头瓶子,洗刷得干干净净。材料?更别提了。从楼下花坛里挖了点半干不湿的土,捡了几块邻居装修扔掉的白石子,又去河边抠了一小块带着青苔的泥巴。我就这么徒手,把土堆在瓶子底,歪歪扭扭的,算是山丘;把石子零零散散地嵌在土里,算是河滩;最后,把那块宝贝似的青苔小心翼翼地摁在最前面。做完这一切,我拧上瓶盖,对着灯光一看——那真是一团糟。土是土的,石头是石头的,苔藓是苔藓的,它们彼此陌生,毫无生气,像个没人打理的荒废角落。
我有点沮丧,但更多的是不甘心。我意识到,造一个世界,光有热情不够,还得有“理”。这个“理”,不是书本上那些大道理,是让这个小天地自己能“活”起来的规矩。
我开始较真儿了。我扔掉了那个罐头瓶子,正儿八经地买了一个弧面的玻璃缸。我研究什么叫“底砂”,什么叫“水苔”,什么叫“轻石层”。原来,直接把土放进去是会烂根的,底下必须有一层疏水的隔层。我像个小学生一样,老老实实地铺上一层轻石,又盖上一层水苔,防止上面的种植土掉下来。光是打这个基础,我就花了整整一个下午,一层一层,压实,抹平。
然后是最重要的——摆弄砂石,塑造山河。
我把买来的各种沙子、碎石倒在白纸上,像画家挑选颜料。深色的溪流沙,我用来铺一条想象中的小河床;粗粝的青龙石,我敲敲打打,选出有棱角的那几块,叠成陡峭的悬崖;细腻的白沙,我则把它撒在向阳的一面,做成宁静的沙滩。这个过程,是最迷人,也最磨人的。它不是简单的堆放,而是“对话”。
我用一把小镊子,夹起一块石头,左放放,右摆摆,总觉得不对。退后一步,眯着眼看,再调整。那块主石,我反复挪了不下十次。一会儿觉得它太突兀,破坏了整体的和谐;一会儿又觉得它不够气势,撑不起这片天地的骨架。我趴在那里,脖子都酸了,世界里只剩下我和那些石头、沙粒。时间慢了下来,呼吸也轻了。终于,在某个瞬间,当我将一块长条形的石头斜倚在主石旁边时,整个画面的重心一下子稳了,前后有了层次,仿佛它们天生就该长在那里。
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。我不是在创造,我是在发现,是在帮这些沉默的石头,找到它们在这个小世界里本该在的位置。
山河初定,接下来是请进“居民”。植物不是随便种的。我选了极小的网纹草,它的叶子比米粒还小,红红的脉络,像害羞的血管;星星苔藓被撕成极小的一撮一撮,用牙签蘸着水,仔细地贴在有土的石缝里。最后,我在那片白沙滩上,放了一个垂钓的老翁微缩模型。他戴着斗笠,披着蓑衣,一根鱼竿伸向那片由一片深蓝色玻璃片代表的“湖水”。
全部完工,是在一个深夜。我洗净玻璃缸壁,用小小的喷壶细细地喷了一层水珠。然后,我关掉房间所有的灯,只打开藏在缸顶的那盏小射灯。
光落下来的那一刹那,我屏住了呼吸。
一切都活了!灯光给山石投下了深邃的阴影,峡谷显得幽深而神秘。水珠在苔藓和草叶上晶莹闪烁,像清晨的露水,又像刚刚停歇的雨。那片蓝色的“湖面”,波光粼粼。而那个垂钓的老翁,静静地坐在他的世界里,仿佛已经坐了一千年,还要继续坐下去。时光,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中,仿佛凝固了。它那么小,小到可以放在我的书桌上;又那么大,大到能装下我所有的烦闷与焦躁。
我久久地凝视着它,心里那片空落落的地方,不知何时,已被这个由我亲手唤醒的、宁静而完整的世界,温柔地填满了。原来,治愈一颗心的,未必是远方的山河,也可以是掌心里的乾坤。往后的日子,每当我觉得疲了、倦了,我就会坐到它的面前。看着那片我亲手堆砌的山,我亲手铺就的沙,还有那个永远在垂钓的、安宁的老翁,我的心便会慢慢地沉静下来。
这个世界,它不会说话,却告诉了我许多。它让我知道,美可以在方寸之间生长,秩序可以在混乱中建立,而宁静,就藏在我每一次专注的呼吸里,藏在我指尖流淌过的砂石之间。它是我为自己造的一个梦,一个随时可以走进去,安放身心的、温柔的故乡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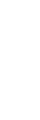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