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回来啦?快洗手,准备开饭!”母亲回头看见我,眼角笑出了深深的褶子。我放下行李,目光习惯性地扫向那个靠窗的座位。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空了。
那是奶奶的座位。
往年这个时候,她总是早早地坐在那里,穿着那件藏蓝色的罩衣,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手里要么在剥着一颗花生,要么就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忙进忙出。那个位置光线最好,又避开门口的穿堂风,是全家公认的、属于她的“专座”。此刻,那把厚重的木质扶手椅空荡荡地摆在那里,椅面上没有垫子,露出深色的原木,像一个突兀的句号,停顿在满屋的喧嚣与喜庆里。
记忆像被热气熏开的潮雾,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奶奶在的时候,那个座位从来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。开饭前,那里总堆着她给我们这些小辈准备的红包,虽然数额不大,但都用红纸包得整整齐齐;饭桌上,她的筷子仿佛长了眼睛,总能把最好的那块鱼肚子肉、最瘦的那片腊肉,精准地夹到我们碗里,嘴里还不住地念叨:“多吃点,工作辛苦,看都瘦了。”我们推辞,她就假装生气,直到我们乖乖吃下,她才心满意足地抿一口黄酒。
印象最深的是我上高中那年的年夜饭。我跟父亲因为选科的事情争执起来,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大家都埋头吃饭,不敢出声。是奶奶,她用她那布满老年斑的手,轻轻转了转桌上的转盘,把父亲最爱吃的红烧肉转到他面前,又把我这边有点够不着的糖醋排骨往前推了推,然后用一种极平常的语气说:“大过年的,有什么事,吃完这顿热乎饭再说。天大的事,也大不过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。”她没讲什么大道理,就那么两句话,配上她慢悠悠的动作,像一块温柔的磁石,把快要散掉的气氛又稳稳地吸了回来。那个座位,仿佛是整个家的定盘星。
去年春节,奶奶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。她依旧坚持坐在那个位置上,但吃得很少,手也有些抖。母亲给她换了轻巧的勺子,她把一块她最拿手的蛋饺颤巍巍地夹到我碗里,小声说:“趁热吃,奶奶今年力气不够,味道可能不如从前了。”我低头咬下去,馅料依然鲜美。那时我竟天真地以为,这样的味道,这样的团圆,会年年都有。
思绪被一阵喧闹拉回。侄子侄女们吵着要喝饮料,妹妹和妹夫在争论春晚哪个节目好看,父亲招呼大家:“都愣着干什么,坐,坐啊!”一家人陆续落座,谈笑声、碗筷碰撞声、电视里的歌舞声,交织成一片熟悉的背景音。热闹是真热闹,可我的目光,总是不自觉地飘向那个空着的座位。它像一个无声的漩涡,把周遭所有的声音和色彩都吸进去了一点。
母亲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走神,她拿起一个空碗,默默地盛了小半碗暖锅里的汤,又夹了一只奶奶最爱吃的肉圆,轻轻放在那个空位前的桌面上。她没有说话,但这个动作,让桌上瞬间安静了几秒。父亲端起酒杯,清了清嗓子,想说点什么祝酒词,张了张嘴,最后只化作一句:“来,吃菜,吃菜,都凉了。”
那顿饭,我们吃得比往年都要“努力”。大家似乎心照不宣,拼命地找着话题,说着工作中的趣事,谈论孩子的学业,笑声也比往常放大了几分。可我知道,每个人的心里,都装着那把空椅子。它提醒我们,团圆这个词,从此有了一点点难以填补的缺口。它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圆,而像一个被小心翼翼咬了一口的月饼,形状变了,但那份甜腻的寄托,还在。
吃完饭,我主动收拾碗筷,走到那个空座位旁,手指无意间拂过冰凉的椅背。恍惚间,我好像又看见奶奶坐在那里,对我温和地笑着。我忽然明白,那个座位,或许会一直空下去了。我们不会再安排任何人去坐它,因为它不属于空间,而属于时间,属于记忆。它空在那里,是一种承认,承认生命中有无法挽回的逝去;它空在那里,也是一种存在,以一种无比清晰的方式,告诉我们,她曾经那样重要地,参与过我们每一个团圆的时刻。
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,新的一年,真的来了。屋里的暖气很足,家人的脸庞在灯光下泛着红光。我端起茶杯,抿了一口。那个空座位,就让它空着吧。有些空缺,本身就是最深沉的团圆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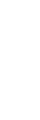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