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哥哥,这碗怎么卖?”我问。
大爷抬起浑浊的眼睛,慢悠悠伸出三个手指头:“三十。都是以前厂里剩下的,现在没人要喽。”
我摩挲着碗边,确实能摸到细微的凹凸不平。碗底的青花勾勒得歪歪扭扭,像小孩子学画的线条。正要放下,却看见碗心有一道极浅的裂纹,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
“这都有裂了还卖三十?”我指着那道裂纹。
大爷笑了,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:“老弟啊,这裂纹才是它的来历。六十年代厂里烧窑,那天突然降温,一窑碗十有八九都裂了纹。老师傅说,这是泥巴记得那天的冷。”
我心里一动,最后还是买下了这个带裂纹的碗。
回到家,我把碗放在餐桌上最显眼的位置。妻子看见了直摇头:“花三十块买个破碗,你这毛病什么时候能改?”
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买。可能就是大爷那句话打动了我——泥巴记得那天的冷。这裂纹不是瑕疵,是记忆。
从那天起,我像是着了魔,开始到处寻找这种“不完美”的碗碟。每个周末,我都往古玩市场、旧货摊跑。去的次数多了,渐渐认识了不少卖旧碗碟的老人,也听来了不少故事。
有个姓李的老奶奶,九十多岁了,还坚持每周日出摊。她卖的碗碟都是她年轻时在陶瓷厂工作的收藏。有一次我看中一个白瓷碟,碟心有一小片釉色特别深,像晕开的墨迹。
“这个啊,”李奶奶眯着眼睛说,“是七六年唐山地震那天烧的。我们正在上釉,地动了,我的手一抖,釉就洒多了。后来听说唐山……这碟子我就一直留着,没舍得卖。”
她说话时,枯瘦的手指轻轻抚过那片深色釉,仿佛在抚摸一段沉重的往事。那天我买下了这个碟子,李奶奶却只收了我十块钱。“给你讲讲它的来历,它就值这个价了。”她说。
还有一次,我在城南的旧货市场淘到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。卖碗的老爷子说,这碗跟他三十多年了。“年轻时在工地干活,都用这碗吃饭。这缺口是有一年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的,碗磕破了,人没事。”他笑得豁达,“现在老了,干不动了,这碗也该换个主人了。”
我把这些碗碟都带回家,小心翼翼地摆在书房的多宝格里。妻子说我疯了,净往家捡“破烂”。可在我看来,每一个碗碟都承载着一段人生。
最让我动容的是一对青瓷小碟,我从一个即将拆迁的老小区里淘来的。卖碟子的老太太姓王,快八十了,因为要搬去儿子家,不得不处理掉一些老物件。
“这俩碟子是我结婚时婆婆给的,”王奶奶说,“那时候穷,买不起成套的,就这一对。我和老伴用了五十年。”她顿了顿,眼睛望向窗外,“他去年走了,吃饭时我再也不用两个碟子了。”
我看见其中一个碟子的边沿有个小缺口,便问是怎么回事。
“那是十年前,我们吵架,我气得把碟子往桌上一摔。”王奶奶笑了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“结果他没生气,反而说:摔得好,这下这个碟子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了。从此我们再也不吵架了。”
我买下这对碟子时,王奶奶反复叮嘱:“它们是一对的,千万别分开。”
现在,我的多宝格里已经摆了二十多个这样的碗碟。每个都有瑕疵——或是裂纹,或是缺口,或是釉色不匀,或是形状微歪。但每个瑕疵背后,都藏着一段鲜活的人生。
那个带裂纹的青花碗,我用来养水仙。水仙的根须透过裂纹隐约可见,别有一番韵味。有深色釉斑的白瓷碟,我用来盛放糖果,那片深色恰好衬得糖果更加鲜艳。缺口的搪瓷碗成了我的笔洗,青瓷小碟则一个放茶点,一个放印章。
朋友们来我家,总会对我的收藏感到好奇。当他们听说每个碗碟的故事后,都会沉默片刻,然后轻轻拿起一个,细细端详。
“原来瑕疵也可以这么美。”一个朋友感叹道。
是啊,这些碗碟就像人生,完美无缺固然好看,但有故事、有经历、有伤痕的,才更动人。它们易碎,却顽强地留存至今;它们有瑕,却因此独一无二。
有时夜深人静,我会独自坐在书房,就着一盏台灯,慢慢擦拭这些碗碟。手指触碰到那些裂纹、缺口时,仿佛能感受到它们经历过的岁月——那些寒冷的窑变之夜,那些颤抖的手,那些争吵与和解,那些生离死别。
现在我也老了,头发白了,腰也不如从前挺直。但我越发懂得,就像这些碗碟,生命中的每一道裂纹、每一个缺口,都不是失败的标记,而是我们来过、爱过、活过的证明。
前几天,我又去菜市场找那个卖碗的大爷,想再买几个。旁边摊位的人说,大爷去年冬天就走了。“他卖了一辈子碗碟,临走前还说,最舍不得的就是那些别人看不上的残次品。”
我站在曾经遇见大爷的地方,心里空落落的。秋风卷起几片落叶,打着旋儿落在当年铺蓝布的位置。
回家路上,我特意去瓷器店买了个完美无瑕的白瓷碗。碗身光洁如玉,釉色均匀,找不到任何瑕疵。可把它放在多宝格里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它太完美了,完美得没有故事,没有温度。
第二天,我把这个新碗送给了邻居刚结婚的小两口。他们高兴地收下了,说这碗真漂亮。
而我,继续用着我的旧碗吃饭。端起那个带裂纹的青花碗,米饭的热气从裂纹间袅袅升起。我忽然明白,我收藏的不是碗碟,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。这些易碎的、有瑕疵的碗碟,比任何完美的器物都更接近生活的本质。
就像人生,我们都在磕磕碰碰中前行,留下各自的裂纹和缺口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,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,让生命有了温度和记忆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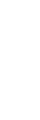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9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6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4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2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