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是周五下午三点多,本来嗡嗡作响的车间突然传来“嘎吱”一声怪响,接着就是让人心慌的寂静。王师傅从机床后面探出头,抹了把脸上的油污:“完了,老伙计罢工了。”
这台M1432外圆磨床,比我的工龄还长,厂里人都叫它“老磨”。它要是停了,后面好几道工序都得停摆。主任围着机床转了两圈,眉头皱得能夹住螺丝刀:“下周一还有批急活,谁能看看?”
我往前站了一步:“我试试吧。”
说实话,我心里也没底。虽然干维修十几年了,但这种老机床就像个脾气古怪的老头,毛病藏得深。
周六早上七点,我就到了车间。偌大的厂房就我一个人,老磨静静地趴在角落里,失去了往日的生气。我先从最简单的开始,打开电箱闻了闻——没有焦糊味,好事。万用表量了一遍电压,都正常。那就不是电的问题。
接着检查机械部分。我用手转动砂轮轴,转不动;用扳手轻轻敲了敲,还是纹丝不动。这种情况,八成是主轴卡死了。拆主轴是个精细活,得像拆炸弹一样小心。
我先把防护罩一颗颗螺丝卸下来,这些螺丝都老了,有的已经滑丝,得用冲击起子慢慢敲。拆开罩子,里面的情形让我倒吸一口凉气——黄油早就干成了硬块,混着金属碎屑,像水泥一样把轴承糊住了。
最麻烦的是拆主轴螺母。它已经在那个位置呆了二十年,根本不愿意下来。我往螺纹里滴渗透油,等了半小时,再用加长杆的扳手,整个人吊在上面使劲。汗水顺着安全帽带子往下滴,在工作服上洇开深色的印记。
“咔——”终于松动了。那一瞬间,我差点从工作台上摔下来。
等到把主轴完全取出来,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。我去食堂扒拉了口饭,又回到车间。下午的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,在满是油污的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带。
清洗轴承座是最需要耐心的。我用柴油一点一点地浸泡,用小刷子仔细刷洗每个油孔。那些金属碎屑很小,比头发丝还细,但它们就能让整台机床瘫痪。这让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:“机器不会骗人,你糊弄它,它就糊弄你。”
就在我专心清洗的时候,车间门开了,看门的老张头端着个饭盒进来:“就知道你还在。给你带了几个包子,还热着。”
我们坐在工具箱上吃包子,老张头说:“这台老磨床,当年可是咱们厂的功勋设备。八九年引进的,那会儿全厂就它会磨精密轴。”他指着机床铭牌,“这些年来,它磨过的零件,怕是能绕地球一圈了。”
我看着这台布满岁月痕迹的机床,突然觉得它不再是一堆冰冷的钢铁。那些划痕,那些油污,都是它为我们厂付出的证明。
周日一大早,我带着新轴承来到车间。安装比拆卸还要小心——轴承必须绝对平行地压入,稍微歪一点,前功尽弃。我用铜棒轻轻敲击,靠听声音判断是否到位。那“叮叮”的声响在清晨的车间里格外清脆。
所有的零件清洗完毕,该上油的上油,该更换的更换。当我最后把主轴装回去的时候,太阳已经西斜。拧紧最后一颗螺丝,我的手竟然有点抖。
推上电闸,按下启动按钮。
“嗡——”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,砂轮平稳地转动起来,声音柔和而有力。我拿过一根废轴试磨,出来的表面光洁如镜,精度完全达标。
那一刻,我靠在机床旁,点着一根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不是兴奋,而是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窗外,夕阳把整个厂区染成了金色,下班的铃声远远传来。
周一早上,主任早早来了,看到老磨又在正常工作,拍了拍我的肩膀,什么都没说。但我知道,那台老磨床还会继续运转下去,就像我们厂里这些老师傅一样,也许不那么先进,也许偶尔会闹点脾气,但只要用心对待,它们就会一直默默地贡献力量。
现在每次经过老磨,我都会多看它两眼。它发出的嗡嗡声,在我听来,就像是一首老歌,唱着关于坚守、关于传承的故事。而我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,真好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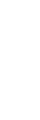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09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3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