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的女孩子下腰、劈叉,像柔软的柳枝,轻轻松松就弯成了漂亮的弧度。我呢?站着弯腰,手指尖离膝盖还有一大截,体育课坐位体前屈,那标尺上的数字,永远是负的。记忆里最清晰的,是幼儿园那次文艺汇演选拔。老师让我们学着电视里的小天鹅蹦跳,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,胳膊腿却像生了锈的机器人,一顿一顿的。老师看着我,那眼神我至今都记得,不是责备,是一种混合着无奈和好笑的神情,她轻轻拍了拍我的头,说:“这孩子,挺认真的,就是……嗯,好像没什么跳舞的天分。”
就这一句“没天分”,像一枚小小的、冰冷的标签,“啪”一声,贴在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小学、初中,但凡有文艺活动,我永远是台下鼓掌的那个。看着同学们在聚光灯下翩然起舞,我心里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,又痒又疼。我不是不喜欢,我是被“判定”为不行。
可心底那点不甘心,像一颗被石头压住的草种子,它总要寻个缝隙钻出来。高一那年,学校街舞社招新,宣传海报做得特别酷。我在摊位前徘徊了整整一个中午,心脏“咚咚”直跳。最后,是社长,一个染着栗色头发的爽朗学姐,一把拉住我:“同学,感兴趣就来试试嘛!”
这一试,就开启了我长达八年的“死磕”之路。
我成了社团里最“著名”的钉子户。著名,不是因为跳得好,而是因为“差得突出”。同一个动作,别人十分钟学会,我得练上一百遍。扭胯,我像腰间别了根棍子;wave,我做得像触电。镜子里的自己,笨拙得让人想发笑。排练时,我总是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,有时甚至只是一个背对观众的角色。队友们都很善良,从不说我什么,但那种无形的隔阂,我能感觉到。休息时,她们聊着哪个动作如何衔接更流畅,我插不上嘴,只能默默地在一旁压腿。
我开始给自己开小灶。放学后的舞蹈房,熄灯最晚的一定是我。我把一个动作分解成无数个定格,用手机拍下来,一帧一帧地对比教学视频,看自己的胳膊肘角度差了几度,膝盖弯曲的时机晚了零点几秒。压腿是最痛苦的,那条“硬筋”被强行拉伸的感觉,像被人用钝刀子割,疼得我额头抵在墙上,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,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,在脚下的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。
我妈来看过我一次,躲在门缝后头。回家后,她红着眼眶给我炖了一锅排骨,说:“闺女,咱不跳了行不行?看着太遭罪了。”我嘴里塞着排骨,含糊不清地说:“妈,你不懂,痛快着呢。”
是真的痛快。那种和自己较劲,感觉身体的壁垒被一点点凿开的滋味,有一种近乎自虐的快感。八年,将近三千个日夜。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崴脚、肌肉拉伤,贴过的膏药加起来能绕我们排练室一圈。我经历了大学舞团的淘汰,又从一个后勤人员重新爬回正式队员。我经历了找工作时的迷茫,把舞蹈鞋塞进行李箱最底层,以为梦想就此终结。可工作稳定后,第一个念头竟然是:附近哪里有舞蹈房?
直到去年,公司要组织节目参加省里的行业汇演。负责文艺的老师在内部征集,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举了手。当我和其他几位同事站在排练室时,老师看着我们,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,她微微皱了皱眉。那一刻,童年那种熟悉的、被审视的感觉又回来了,冰水一样浇遍全身。
但我没有退缩。音乐响起,我跳了起来。我不再是那个手脚不协调的小女孩,也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角落的替补。八年死磕磨出来的东西,在这一刻融进了我的每一寸肌肉里。节奏、力量、控制……它们成了我身体的本能。一曲跳完,排练室里安静了几秒,然后,那位老师带头鼓起了掌。她走过来,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赞赏:“你练了多久?”
“八年。”我说。声音平静,心里却像有什么东西,轰然炸开。
登上省级剧院舞台的那天,候场时,我的手心还是凉的。但当追光灯“啪”地打在我身上,视野里一片白茫茫,只剩下音乐和自己的心跳声时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我没有去想任何一个动作,只是尽情地跳着,像一只终于破茧的飞蛾,笨拙地、却用尽全力地扑向那团属于我的光。
台下有没有掌声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谢幕时,我深深鞠躬,额头几乎触到膝盖。那一刻我才发现,原来我早已不是那个弯腰摸不到脚的孩子了。
八年,我用时间这把钝刀子,慢慢地磨,终于把“没天分”这三个字,从自己身上磨掉了。它留下的,不是光滑的完美,而是一道道深刻的、粗粝的痕迹。这些痕迹,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天赋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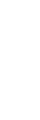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