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是从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开始的。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,阳光透过窗格子,在水泥地上画出明亮的方块。我正收拾着碗筷,桌上的手机就响了,屏幕上跳动着“爸爸”两个字。我心里还嘀咕,老爷子今儿个怎么晌午就来电话了。接起来,习惯性地“喂”了一声。
那边没有回应。只有“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”,平稳、规律、冰冷。
我以为信号不好,或是他老人家不小心碰到了重拨键。挂了,等了一会儿。手机立刻又响起来,还是他。再接,依旧是那片忙音。从那以后,这部手机,就再也没能传出过父亲叫我的小名,或是任何一句别的话。
头几天,我们都以为是手机坏了。我哥拿去维修店,师傅拆开来看了又看,说硬件没问题,就是有点旧了。我们给他换了个新手机,办了新卡,满怀希望地把新号码存进他用了十几年的旧手机里。我亲手教他,哪个键是接听,哪个键是挂断。他戴着老花镜,学得很认真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绿色的,接;红色的,不接。” 我看着他布满老年斑、微微颤抖的手,心里一酸。
新手机开通那天,我们全家围着他。我站在阳台,用我的手机打给他。他手里的新手机亮起来,唱起他最爱听的黄梅戏。他有些手忙脚乱,终于在大家的鼓励下,按下了那个绿色的图标。我们把呼吸都放轻了,满心期待地等着。
传来的,还是那几声“嘟——嘟——”。
那一刻,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凝住了。我母亲最先别过脸去。我哥不死心,抢过电话,对着话筒大声地“喂!爸!听得到吗?” 回应他的,只有那不变的节奏。父亲举着手机,茫然地看着我们,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,他不明白,为什么我们能说话,他却只能制造这片空洞的忙音。
我们带他去了最好的医院,耳鼻喉科、神经内科,能查的都查了。医生的诊断书写得清清楚楚:听觉器官未见器质性病变,推测为老年性神经系统退化引发的功能性失联。说人话就是,他的耳朵能听见,他的嗓子能发声,但他的大脑,那个负责把听见的转化为理解、再把想说的组织成语言的精密中枢,有一条线路,悄悄地断掉了。他被困在了自己的身体里。
从此,我们家的日子,就绕着这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转了起来。
那声音成了他的呼吸,他的心跳。起初,它让我焦躁。我在公司开会,手机在口袋里震动,我知道是他,不能不接。可接起来,对着那片忙音,我所有的话都像石子投入无底深渊,连个回响都没有。我得强压着心里的火气,和客户陪笑脸,说“不好意思,有点急事”。挂了电话,只觉得一阵无力。
我母亲更是受不了。她是个爱说话的人,和父亲拌了一辈子嘴。现在,吵架的对象没了,只剩下一个永远在“通话中”的丈夫。她常常拿起家里的座机,听着里面的忙音发愣,然后默默地放下,转身走进厨房,水龙头开得哗哗响。我知道,她是在用水声盖住那让她心慌的寂静,或者说,盖住那比寂静更让人难受的忙音。
最让人心疼的是父亲自己。他变得越来越沉默,眼神常常是空的。他依旧每天给我们打电话,一遍,两遍,十遍。他固执地认为,只要他拨出去,总能有一次,能重新连接上我们。他拿着手机,在屋子里踱步,从客厅到卧室,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老兽。有时,他会对着话筒,极其费力地发出一些“啊……哦……”的音节,脸憋得通红,青筋都暴起来。那不成调的声音混在规律的忙音里,听着让人心碎。
我们开始尝试用别的方式和他交流。写字。我买了一大叠白板和各种颜色的水笔。起初,这办法似乎有效。问他“吃饭了吗?”,他会在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个“吃”字。问他“想下楼走走吗?”,他会画个圆圈,代表“好”。
但很快,这扇刚刚打开一条缝的窗,也关上了。他写的字越来越乱,越来越认不出。一个“我”字,可能少了那一撇,或者“饭”字缺了那边一点。后来,干脆变成了一团毫无意义的线条。最后,他连笔也握不住了。那支黑色的水笔从他指间滑落,在地上滚了几圈,停在墙角,再也不被他拾起。
我们之间,仿佛隔着一堵越来越厚的玻璃墙。他在那头,我在这头。我看得见他所有的焦急、无助和渴望,却碰不到他,也听不见他。那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忙音,就是这玻璃墙唯一的回声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下午。我儿子,他五岁的小孙子,坐在地板上搭积木。父亲的手机又响了,他照例接起,听着里面的忙音。小家伙忽然抬起头,眨着亮晶晶的眼睛,对他爷爷说:“爷爷,你的电话在唱歌呢!嘟——嘟——,像不像小火车?”
我父亲愣住了,低头看着孙子。那一刻,他浑浊的眼睛里,好像有了一点光。
孩子的话,像一把钥匙,猝不及防地打开了我心里那把沉重的锁。是啊,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当作一种故障,一种断绝的信号呢?为什么不能像孩子一样,把它听成一种特别的“歌声”?
从那天起,我开始学着“听”这忙音。
我不再急着挂断。当那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再次响起时,我会走到窗边,看着楼下车水马龙,静静地听。我听着那声音里的平稳,那是一种生命的韧劲,他还在,他还在努力地向我发出信号,这就够了。我听着那声音里的空白,那空白里,开始填进很多东西。
我听见了几十年前,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,载着童年的我,车铃“叮铃铃”地响,他宽厚的后背,为我挡住了所有的风。我听见了少年时,我因为考试失利把自己关在房里,他轻轻敲门,在门外说:“没事,爸在这儿。” 我听见了我结婚那天,他紧紧握着我的手,什么也没说,只是红着眼圈,重重地拍了两下我的肩膀。那力量,至今还留在我肩上。
所有他曾经对我说过、而今再也说不出的话,都在这片忙音的空白里,汹涌地回荡起来。那不再是空洞的提示音,那成了他一生沉默的、厚重的爱的回响。
我开始对着这片忙音说话。
“爸,今天天气真好,我推你下去晒晒太阳吧。”
“我升职了,工作有点忙,但一切都好,你别担心。”
“你小孙子今天在幼儿园得了一朵小红花,臭美得不行,跟你当年夸我一模一样。”
“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,火候正好,晚上你多吃几口。”
我知道他无法用语言回应我,但每次,我都能从电话那头,听到他呼吸节奏细微的变化。有时是稍微急促一点,有时是长长地、舒缓地一声。有时,我甚至会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极轻微的“嗯”。这对我来说,就是最珍贵的回答了。
这部手机,这部只会发出忙音的手机,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一座最奇特的桥。它看起来是断的,但实际上,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固。它逼着我不再用耳朵去听,而是用心去听。我听懂了他的沉默,听懂了他无言的注视,听懂了他布满老茧的手的温度。
如今,那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声音依旧每天都会响起。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,像背景音乐,不再刺耳,反而让我安心。它提醒我,他还在。它告诉我,有些联系,是任何疾病和时间都无法切断的。
这忙音,是他留给我的一首无字的歌。歌里,有他骑车载我的那个下午,有他拍在我肩上的重量,有他所有说不出口的牵挂和爱。它在我心里,成了一道永久回响。这回响,将一直持续下去,直到有一天,在我的世界尽头,与他的沉默,真正地重逢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风暴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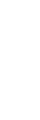 风暴文章
风暴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8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1)
3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10)
4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04)
5专注美妆领域,我用成分创新打开市场突破口